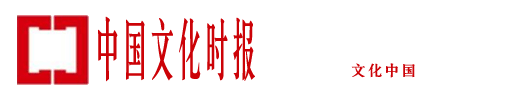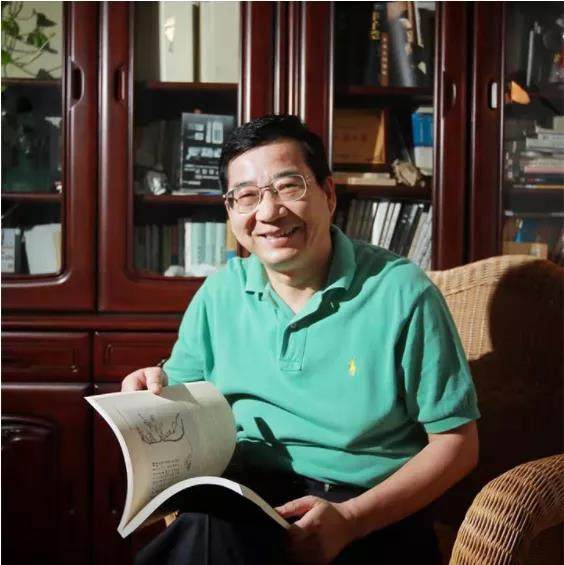
苏北,本名陈立新,安徽天长人。著名散文家,汪曾祺研究专家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安徽大学兼职教授。著有《苏北作品精品集》(六卷)。散文集《城市的气味》《忆•读汪曾祺》。

刘学懿作品
一
我曾写过一篇短文《我和山的一些关系》,历数与我发生过关系的一些山水。其实,我和酒的关系,也是可以写一篇文章的,我与酒周旋久矣!
我其实是不善饮的。我的兄妹中,只有我一个人能喝一点酒。能喝一点,也只是二三两而已。我的大哥是个卡车司机。卡车司机多较为辛苦,应该是喝酒的,可他一辈子滴酒一沾。我二哥是税务干部,在二三十年前你想想看,应该是吃香的喝辣的,可他见酒就跑,无奈被逼迫喝下一杯,要睡一天才能缓和。我妹妹下岗,妹夫酒量惊人,可她从来不喝。我的父母一辈子更不沾一星酒星。
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沾酒的,现在已无从考据。大约初中时,我们县里建了一个啤酒厂,一时成了新闻。因为一个县的人,过去对啤酒闻所未闻。因当地生产,那时是可以打散装的,也比较新鲜。我父亲好奇,让我到烟酒公司打了一点回来。夏天的黄昏,在自家院子里摆上小桌,豆子稀饭和着咸鸭蛋、毛豆炒臭咸菜(其味甚佳),开始喝了起来。初喝味极难闻,第一口的印象和所有第一回喝此物的人没什么两样:“什么鸟味?像马尿。”
就这样,在严热的蝉鸣声中,我们且饮且品咂,一人喝了大半碗(都是用碗喝的,真是大碗喝酒),马上有了感觉,就是我们县的人土话说的:“脸红脖子粗”,仿佛自己不是自己,人变得“有些木”。
十八岁以后参加工作,我被分配到邻县的一个小镇,那个小镇是个山区,也是老区,于是酒风极盛。到那工作不久,即投入到水深火热的酒场生活之中了。
这个小镇属皖东,名叫半塔。古书记载,曾有过一个古塔,可惜不知何年,叫雷劈了。半塔离我县不足百公里,可民风比我们那里已彪悍了很多,我们就觉得他们已比较“侉”。他们开口闭口“干哈干哈”,就是干什么的意思。叫小孩也不叫孩子,而是一口一个“这熊孩子这熊孩子”。
他们喝酒,盅子都比较小,一个盅子大母指正好可以套进去。可是他们一喝都是四个、六个,或者八个。他们喝酒不叫喝,叫“斗”。——“斗一个?”“好,斗一个。”——其实不是“斗”一个,而是“斗”一回。因为“斗一个”下来,有来有往,也至少四个才行。
“斗”字很妙。两个杯子一碰,岂不是一“斗”?从中国古人开始,其实还是蛮会玩的,在生活中创造出很多乐趣。比如,在广袤辽阔的中国大地上,从西到东,斗羊、斗牛、斗鸡、斗狗、斗猴,等等。什么都是可以拿来斗一斗的。反正就是一对一的捉对厮杀。两只羊打两条牛打两只鸡打两条狗打两只猴打。有的便形成了文化、形成了风俗,形成了“节”,到“那个时候”总是要“斗一斗”的。我们省的宿县民间就有“斗羊”习俗;在遥远的西方,斗牛更是形成“西班牙风格”,成了时尚,令人向往。
在喝酒上,我疑惑,“斗”字也可能是“逗”。或者就称之为“逗”,也无不可。因为饮者之间,互相逗趣,你逗逗我,我逗逗你。反正是件快乐的事。不管是“斗”还是“逗”,听起来都是不错的。
这里估且还是“斗”罢。
斗酒,是人和人斗的直接表现。不是说嘛,人和人斗其乐无穷。是的,斗的不仅仅是酒,还有身体、胆量、气概、雄心、友谊、快乐、仇恨……你说什么都可以。
一场酒下来,也不仅仅是这样干“斗”,还辅以各种游戏:老虎杠子、猜拳和猜火柴棒子,等等。我们最初学习的是古老的方式:猜拳,也叫划拳。别小看了这划拳,局外人见满桌大呼小叫,扯着嗓子喊。其实,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游戏。它是人在兴奋的状态下的一种斗智斗勇斗蛮斗憨的工具。赢者得意骄傲自满:“小样,跟我搞!”输者懊恼、后悔、不服,还有攀本、报复的心理:“再来,我就不信?”于是一而再,再而三。
二
我学喝酒主要是跟一个姓沈的会计。他那时大约四十来岁,生了五个娃,瞎了一只眼。娃都是他亲生的,这毫不怀疑,那只眼是如何瞎的,不得而知。我们仿佛觉得他天生就瞎了一只,因此也不为奇。
那时镇上的单位都是“家连店”,——前面办公后面住家。沈会计也住在后面家属区内,可是他在办公楼的山墙搭了个小棚子,既当厨房又顺便开了个小卖部,卖些油盐酱醋之类,因为他的老婆没有事做,整日待在家里,孩子又多。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。于是我们的酒场,多是在他家,由他老婆炒几个小菜,我们则在他家门口的一张小桌子上,喝将起来。
参加喝酒的多为同事。下班了,谁没有事,就过来喝两杯。小镇上的人,多较悠闲。有个叫邓崇的信贷员,那时大约也才二十五六岁,因也是单身,于是他来喝的最多。邓崇家在县城,父亲还是个什么官,他就显得神气一点。人是极聪明的,口齿又伶俐。只是他不喜欢谈对象,他曾将一个女的一寸小照片给我看过,说是他家里人给他介绍的对象。我只记得那张黑白照片上的人头发很黑,辫子很粗。邓崇不屑地对我说:“你说谈对象有什么意思?”我望着他笑。他又说:“是吧?还没有喝酒快活呢!”
邓崇曾教我划“小雨夹雪”。所谓“小雨夹雪”,也就是将拳和老虎杠子交叉进行。一下老虎杠子一下划拳,如此循环往复,既不能出错,也要迅速考虑出什么才能压倒对方。这其实是挺难的。刚开始老虎和拳乱喊一气,总是输。后来好不容易喊出囫囵形了,又脑子跟不上,往往跟在人家屁股后面喊,又是被死逮活捉。这样酒要多喝许多,醉于是成了家常便饭,吐也是不在话下的了。
说到醉酒,此地也自有一套不成文的法则。我们刚到这个小镇时,就甚为奇怪,每到中午,特别是逢节的日子,上午满街的行人,买的,卖的。卖牛,卖羊,卖鸡鸭鱼肉,各色小吃,肩挑担扛,各种吆喝之声不绝于耳,行于街市,磨肩擦踵,而到下午,街上就不见了人影,之后就是好几个醉汉斜卧大街一角的阳光之下,无人去管,行人从边上经过,也视而不见,自顾走去。
日子久了,我问旁人,为何这样?
他们并不为怪,说:“喝醉了,就这样。等他自己醒了,就拍屁股回家了。”
“怎么没人管呢?”
“不用管的。”
“同他一起喝酒的人呢?”
“回去了。”
我懂了这些,日后每每在街上遇见,也不为奇。而且也从来没有听说过,这些倒在大街上的人,出过啥事情。再说,喝醉了,对我也是常有的事。喝吐了,也是不在话下的了。
我每每喝多,就回到房间躺到床上,凝神、数数。凝神和数数其实是两种方法。凝神就是盯着一个地方看,不说话,比如盯着屋顶,或者看住外面的一片树林,或者天上的一片云彩,一动不动。如此数分钟,也许酒劲就能过去。数数就是从一数起,一二三……到十,这么数来数去,数着数着就睡着了。

上甑蒸馏
三
有一年清查社队贷款,我们到村里核账。我和老沈,还有一个张华。张华个子特别矮,可酒量大。小眼睛,眼睛总是红红的,而且喜欢眨。嘴上有两撇小胡子。他开口说话,小眼睛就眨眨的,嘴上的小胡子就一动一动的。张华负责社队贷款,我们跟着他到队长家。核了账,就开始吃饭,那时条件差,也没有什么好吃的,就在队长家代伙,烧了一盆土猪肉,用萝卜烧,又炒韭菜、蒸咸肉、烧扁豆。我们就着大肉喝将起来,喝的也只是当地土酒,那时每个县里都是有一个自己的酒厂的。边喝着边划着拳,张华虽然个子小,可喝起来毫不含糊,小拳划的也不错,队长姓马,也是一个酒鬼,酒量大的惊人。在队长家一直喝到下午两三点,我这时眼睛就不大清楚了。
酒后往回走。虽然是乡村土路,可白土十分干净,村道边密密的杨树,树头哗哗地的都是风。小风一吹,我酒劲上来了,眼睛就黏黏的,我一头钻进路边的小树林,老沈和张华也自顾走去,并没有理我。进了树林,我捡一棵大树,坐下靠在上面。先盯着树顶看,可树转得很,又转来开始数数,一二三……还是不行,于是便慢慢褪下身子,睡在了草地上。草地软软的,很舒服。可草也转了,天也转了。那个天特别的蓝,又特别的高。这么一个大大的蓝天在我眼前转,可我无法欣赏,我一翻身,睡过去一点点,就吐了一地。吐了出来人就舒服了,我又一翻身,捡一块干净的青草,睡下去。一睡就睡着了。等我一觉醒来,天已黑透了。小树林一片虫鸣,青草透出一股清新的香味。我抬头看天,满天的星星,真正是“星斗皆光大”。那简直是个大风景,美极了。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星星,没见过这么一个美丽的辽阔的长天。
我站起来,沿着乡村的泛白的土路,在星光下慢慢往回走。四周静极了,只是远处不时传来几声狗的狂吠。
转眼到了年底,单位安排了一些慰问活动,我们分到了一些米和油。对老同志,还每人买了两瓶酒。那个时候,我们只喝地产酒,还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好的酒,主任叫老沈到供销社批发了两箱泸州老窖,分别给年龄大的送去。镇北头住的退休的老徐和老马,安排我给送过去,我骑上自行车,将四瓶酒挂在自行车龙头的两边,骑上一溜烟飞奔而去。我先去了老徐家,拎上两瓶,三步并着两步跑过去,推开门将酒递给了老徐的老伴,又赶紧出来,因为我记挂着自行车龙头上的那两瓶呢!可一眨眼功夫,挂在龙头上的塑料袋没了。那两瓶酒不见了!我向东追了一气,没有一个人;又向西追了一气,还是没有一个人!
我傻了,酒被偷了!
我哭丧着脸推着自行车回去,见到主任眼泪就流了下来。主任倒笑了,“熊样!莫哭莫哭。没听说嘛,‘二十八九就要到手’,贼也要过年呀!”
为了弥补我的过失,我主动要求年三十不回家,留下来值班守金库。过年食堂都停伙了,我便在老沈家代伙。主任特地给我们值班的留了一瓶泸州老窖。老沈为我们煨了一锅鸡汤。那天我们没有斗酒,而是细细喝着那瓶酒。我不说话,喝下一口,就闭着眼睛想。我们几个守夜的,少有的这样安静。
喝到一半,我推门出来一看,夜已深了。一阵凉风吹过来,我打了一个酒寒,一股香气涌上鼻端,那时的感觉,就仿佛自己有千钧的气概。

*《十月·浓香风雅》栏目由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友情支持